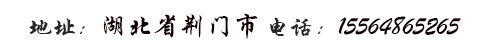夜宿栖霞寺
|
2014年岁末,在红叶凋零的初冬,我走进了栖霞山。 记得年少时,我从父亲口中第一次听说过栖霞山。当时,为了一家人的生计,父亲曾在栖霞山做过工。几十年后的今天,我第一次走进了栖霞山。却不知在哪一条山道上,还留有父亲当年的足印。 “如果不曾相见,人们就不会相恋,如果不曾相知,怎会受这相思的熬煎……”这天下午,在栖霞寺南侧的云水堂,我哼着小曲儿爬上三楼。走过一段空寂无声的楼道,只见后面有个人影一闪,我赶忙回返几步。定睛一看,站在面前的不是别人,正是客居栖霞寺的江都画家刘文锦。“刘大师,我终于找到你了!”66岁的他面色红润,一双剑眉又浓又黑。“这么巧!”“就这么巧!”他乡遇故知,一种欣喜在心头漫漶。 文锦兄把我让进了他的画室,太阳从窗户里照射进来,20个平方米的屋子真叫一个敞亮。我细细地打量着,一只斗笠挂在墙上,几盆兰花诗意舒展,画桌上、画稿上笔墨生香。他向我伸出了三个指头说:“想不到吧,我已在此客居三年。”沏上一壶茶,文锦诚恳地问道:“怎么样,今天请你留宿栖霞寺,好好畅叙一番。”我慨然应允,便请他担任向导,游一游栖霞寺。 一座栖霞寺,半部金陵史。走过舍利塔,穿过千佛岩,岩壁上可见星云大师留下的刻印墨宝。经文锦兄指点,我才知道栖霞寺坐东朝西,左青龙,右白虎,前有象山,后依凤山,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。这里还是星云大师少年时的出家地。一路上山,凋零的红叶铺满了石阶,有风吹过,当年的乾隆行宫已片瓦无存,惟有几块方圆形状的石础,在浩荡的残叶中时隐时现。 下午5点,是用晚斋的时刻。我俩匆忙下山,走进了斋堂。两只碗、一双筷,炒青菜、炒苗豆、烧南瓜、野菜豆腐汤,我和僧人们一样,坐在长条桌旁。一番吞咽过后,我才真正明白,什么叫寡菜清汤。 斋毕,文锦兄邀我在山中散步。观一湖为桃花扇,访一茔为李香君之墓。穿过荒草小径,岭南画家高奇峰的半身雕塑静默无言,“高山仰止”——林森、徐悲鸿当年为其撰写的碑文清晰可辨。刘文锦向塑像三鞠躬,我却想起了葬于北京陶然亭的高君宇。一南一北,一位是画家奇才,一位是英烈志士。秋来,与漫山红叶共舞;冬临,化作红霜隐去。他们的人生虽然短暂,却如斯炽烈,片片红叶千古不绝。 月牙爬上山顶之时,栖霞寺被罩上了丝丝簿雾。在画室里,文锦兄谈及他的“寺中三年”。初来乍到,住持隆相法师赠他三句话:“养好身体,把栖霞寺当家,多出好作品。”随后开示两个字:“放下!”入寺三日,便随法师去宜兴大觉寺拜见星云大师。执弟子礼,他相赠一幅绘有六朵牡丹和五条金鱼的画作《吉祥有余》,竟然暗合星云乐见的“五路财神”,大师欣然笑纳。 远离尘嚣,一切随缘。三年来,受赐法名“能悟”的刘文锦一不拜佛、二不念经,在酣畅淋漓的十八罗汉中坐卧起立,在烟雨濛濛的诗禅画境里驰目骋怀,《第一金陵明秀山》、《十八应真图》、《霓裳羽衣》等书画作品摩肩接踵。他有一个计划,再用三年时间,创作完成栖霞“四十八景图”。 次日初九,恰逢栖霞寺供佛祭天法会。大雄宝殿内香雾缭绕,众僧与居士排列成行,诵经念佛,祭天祈福。我早早穿衣下床,寻声而至。晨6时,祭天法会刚刚结束。在晨光微熹的廊道里,一群裹着袈裟的僧人脚步如风。一位年轻的泰州籍僧人双手合十,告知其戒名叫“能”,便匆匆走进了僧侣的队形。在用早斋时,我四处搜寻“能”的身影,面对清一色的模样,却哪里能寻得到。 离开斋堂,文锦兄在云水堂旁边的楼顶平台上快步疾行。他说:“三年天天如此,闻翠鸟啼鸣,看日落日升。早晚各二十圈,每圈百步。”在他的脚下,长长的足印清晰抢眼,就像一个扁平的“回”字。我兀自想到了隆相住持赠与文锦的四个大字:“定能生悟”。芸芸众生,为何放下,其实,是为了更从容淡定地拾起。 “白云送客,贝叶留香”——在云水堂的画室里,我与文锦兄依依握别。他将一幅刚刚完成的《三羊开泰》图相赠,并请我代他问候家乡的挚友故交。 夜宿栖霞寺,我未能带走这里的一枚枫叶,一如我的父亲当年,但却带着文锦兄的一片深情。星月轮回,一切随缘。人和人一样,又不一样。栖霞山的红叶年年绽放,但又有谁能熟稔每一枚枫叶的模样。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jiangdushizx.com/jdsh/1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古稀老人眼中的公交司机
- 下一篇文章: 悖论式的诗意人生——序曹利民诗集《回音》